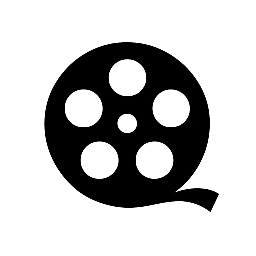1949年冬天,川西的山风已经带着寒意。广汉一座偏僻古寺的院子里,一个刚刚剃度不久的“老和尚”来回踱步,脸上全无出世高人的清净,反而写满了犹豫和焦躁。寺外传来脚步声,有人推门而入:“曾扩情,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这位自称“老衲”的人愣了几秒,嘴唇发抖,却再也说不出当初那句“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”的洒脱话。
这个场景,折射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轨迹:黄埔一期的“老大哥”,“十三太保”中年纪最长的“大太保”,复兴社骨干、特务系统要人,西安事变后锒铛入狱,又在49年拒绝前往台湾,转身披上僧衣,后来再从功德林走上政协会场。曾扩情的一生,不得不说有着一种曲折而又吊诡的戏剧感。
与许多名气更大的军政人物相比,他的名字并不醒目,但把时间线细细排开,会发现他几乎踩在20世纪中国重大转折点的关键节点上:从黄埔军校创办,到权力中枢再到新中国特赦战犯制度的施行,处处都有他的身影,只是姿态在不断变化。

1895年,清朝已风雨飘摇,四川威远这个西南小县里,一户普通人家迎来了一个男婴,这便是曾扩情。童年、少年时期,并无太多传奇之处,但有一点很重要,他走上的是读书求仕的路,而不是纯粹的行伍出身。
进入20世纪二十年代,中国局势动荡,旧制度不断崩塌,新制度迟迟未立。1921年,26岁的曾扩情加入中国。在同龄人中,这个年龄算不上年轻,新思想早已在他脑中打下烙印,他很清楚:靠乡绅、保甲那一套,已经难以应对这个时代。
1924年,他进入北京朝阳大学(亦有称朝阳学院)法律系就读,学习近代法律制度。就在这里,命运突然拐了一个弯。其时,李大钊正在北方积极宣传革命理论,他既是学界前辈,也是实际行动者。曾扩情正是在李大钊的介绍下,和同学胡宗南一道,踏上南下的列车,奔向广州。
这一年,黄埔军校成立。蒋介石任校长,孙中山亲自题写校名,孙中山、廖仲恺、周恩来等人先后参与校务。年轻人蜂拥而至,黄埔一期因而在后来被反复提起。相比那些十几岁的热血青年,时年29岁的曾扩情算是“高龄学员”,在队列里很容易被认作“老大哥”。
进入黄埔后,他不仅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,还被选中担任孙中山的卫。这份工作位置微妙,一边靠近最高领袖,一边接触学校内部的人事和气氛,对后来他对权力和政治的理解影响极大。值得一提的是,黄埔一期中后来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比他小3岁,但在学校里的威望却非一般学员可比。早期的曾扩情,对员印象并不坏,甚至把周恩来看作“恩师”一样的存在。
1925年,军校一期学员毕业。曾扩情留校,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,随同周恩来参加第一次东征。那个阶段,他与许多人关系融洽,思想上也未走向极端。东征沿途风雨飘摇,新旧势力角逐,他一边做政治工作,一边观察各方力量,这种政治嗅觉,后来成为他在党务和特务系统中行走的资本。
局势急转是在1926年前后。“中山舰事件”爆发后,国共关系骤然紧张。军中对人的排斥情绪迅速上升,蒋介石借机收紧军权、整顿党务。这一波政治风向的变化,让曾扩情做出了一个关键选择。
原本与周恩来等人相处良好,他在事件后公开表示要与划清界线,态度之坚决,远超一般人。他很清楚,站队问题已经不再是学理讨论,而是现实生死。这样的选择是否出于信仰,还是权衡利害,各人看法不一,但有一点毋庸置疑:从那一刻起,他彻底倒向了蒋介石。
还在这之前,他就曾同蒋介石等6人,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代表身份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1926年后,蒋介石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,自任会长,指定曾扩情为秘书,负责会务。这既是一份信任,也是一次试探:谁能把这些黄埔出身的军官紧紧拢在自己身边,谁就在军中有了实权。
曾扩情深知这一点,很快就把黄埔同学会变成了替蒋介石造势的平台。他四处活动,劝说黄埔出身的军官把“总司令”视为唯一政治依靠。宣传口径也在不断强化,从“全国军人领袖”扩大到“国家和民族的唯一领袖”,措辞毫不含糊。
有一次,一些身为员的军校同学,在校内张贴标语、散发传单,指责黄埔同学会对队伍中长官虐待学员、贪污受贿等问题袖手旁观,甚至有所包庇。蒋介石对此不仅没有彻查责任,反而严辞保护:“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。”这句话在校内迅速流传开来,也坐实了曾扩情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。
从1928年起,他的仕途明显提速。1928年之后不久,他的职务不断升迁,党务系统中的头衔一项接一项地加到身上。到1931年,他已经成为黄埔毕业生中第一个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。对很多黄埔同学来说,这一步意味着从军人正式跨入党权中枢。
1932年,蒋介石组建复兴社,准备通过这个新组织来整合军队和党内的力量,强化对全国的控制。蒋亲自钦定13名骨干,曾扩情名列其中。这13人后来被外界称为“十三太保”。由于曾扩情年纪最大,辈分又高,被称作“大太保”;胡宗南、戴笠这两位同样声名显赫的“太保”,在他面前也要喊一句“扩大哥”。
这时的他,既有党务头衔,又与特务系统关系密切,在北平、南京等地奔走。到1934年,他出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,主管上北平所有军队的党务、政训工作。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是何应钦,两人同为要员,一度同住,往来甚密。这重门深锁的院落,见证了他的春风得意。
在很多外人看来,这样的上升轨迹要是能稳定维持,未必没有机会一步步走到更高层。只是政治风云变幻,好景总是难以久长。
1936年,西安事变令全国震动,也让曾扩情的人生轨迹再度拐弯。当时,他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,长期跟随蒋介石布置西北地区“剿共”与防共工作,在军政系统内颇有份量。
事变爆发后,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、杨虎城扣留,局势一时扑朔迷离。各方力量都在观望,有人担忧“兵谏”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内战,有人则寄望于借此迫使蒋介石停止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路线,调转矛头对外抗日。
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张学良找到曾扩情。这位东北少帅颇为诚恳,把自己发动事变的初衷——“逼蒋抗日”——细细说明,对他说:“扩情兄,你在党内、军内都有名望,若能站出来,把情况说清楚,对内对外都有好处。”。
曾扩情并非不懂其中风险。他心里清楚,站在张学良一边,就很容易被视为“叛逆同党”;但不站出来,又眼看时局被误解为“兵变夺权”。更何况,早在1935年北平时,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日本签订《何梅协定》,退让严重,这一事件让他心中对“民族领袖”的印象大为受损。内心的矛盾在这时集中爆发。
最终,他选择了出面讲话。面对各方,他公开发表广播讲话,为西安事变“澄清原委”,强调事变本意在于“逼蒋抗日”,不是简单的兵变谋反。这一通讲话,客观上有利于缓和局势,也表现出他对张学良诉求的理解和同情。
然而,蒋介石的态度与他的预期完全不同。事变和平解决后,蒋介石返回南京,心中对“谁站在哪一边”记得一清二楚。在他看来,曾扩情在关键时刻没有坚定站在自己身旁,反而公开为发动者张学良“说好话”,简直就是“倒戈相向”。
不久,蒋介石下令逮捕曾扩情,把他投入军统监狱,甚至一度主张将其处死。倘若这一命令真被贯彻,曾扩情的一生怕是到此为止。只不过,他在内部经营关系多年,平日里对上对下都还算得体,不少黄埔同学对他颇为尊重,这时纷纷出面求情。
狱外,胡宗南为他奔走,串联十多位黄埔同学联名写信,请求蒋介石网开一面;狱中,主管情报与特务工作的戴笠也给予他特殊照顾,对这位黄埔“老大哥”颇为维护。有意思的是,戴笠这个后来被称作“军统头子”的冷酷人物,在对待曾扩情时,却极为客气,这一层关系也从侧面说明他在黄埔、复兴社圈子里的分量。
在多方斡旋下,曾扩情终究逃过一死。只是从那以后,他的仕途已难与往昔相比。表面上仍然有职务、头衔,但在权力核心中的位置已经大不如前。对他个人而言,西安事变既是政治判断的冒险,也是命运转折的起点。
时间往前推到1949年。此时的中国大陆已进入解放战争最后阶段。1949年初,在华东、中原战场节节败退,重庆、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的最后支撑点。曾扩情这时担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,是党务系统在四川的最高负责人之一。
大军入川后,局势急剧崩溃。胡宗南仍在西南一带调动兵力,他惦记着这位“扩大哥”,专门派飞机要把他从四川接走,一同赴台湾。对绝大多数高层来说,离开大陆似乎已经是唯一出路。
然而,曾扩情在这一刻做了一个让很多旧友意想不到的选择。他没有赴约登机,而是悄悄离开成都,潜往广汉。不是去组织起义,也不是公开投诚,而是钻进大山深处的一座古寺,剃度出家。
寺中僧人本就稀少,多一个“老和尚”,外人也不易察觉。曾扩情换上僧衣,口称“老衲”,念经敲木鱼,看上去仿佛真的决意远离尘世。只是仔细想想,他出家时日短暂,既无深厚佛学积累,也难说有真正“放下”的决心,多少带着逃避现实的意味。
不久,进驻当地,开展对原军政人员的清理工作。有人很快发现,这位新近剃度的“和尚”似乎有些来历。部队派人上山查访,进寺一看,果然是那位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。面对,他还故作洒脱地说:“老衲已出家,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,你们抓我作甚?”这种说法,在旧日政坛也许还能唬人,但在当时的军管会看来,这种“假出家”既不新鲜也不奏效。
当听说连削发多年、曾任军统行动处长的宋希濂(资料中多作宋希濂,此处涉及另一位原军统高层宋灰鹤,亦已被捕)也已经被依法控制时,曾扩情意识到,靠一身僧衣躲过清算,根本不现实。这一刻,他所谓的“跳出三界”,瞬间化为泡影。
新中国成立后,中央对战犯和高层人员的处理有明确政策。1950年代初,对主要战犯实行集中管教、劳动改造,在严格监管中进行思想教育。曾扩情因为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,又是党务系统中级别很高的干部,被列入重点对象,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
在这里,政要、军头、特务头目云集,一些曾在旧政权中叱咤风云的人,如今在高墙之内面对新的社会现实。曾扩情因为辈分较高,又有黄埔“老大哥”的名头,在管理所里颇受关注。他的思想转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,而是在长期学习和劳动中慢慢推进。
1959年,形势迎来重大变化。这一年,根据党中央决策,新中国对第一批战犯实行特赦。曾扩情被列入特赦名单。这对那些长期身陷囹圄的人来说,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转折。有一次,管理人员在功德林向他们宣读特赦决定,有人因为多年习惯了“坏消息”,一时竟然以为这是“押解处决”的前奏,心中发凉。曾扩情也曾心如死灰,以为“好话背后还有别的文章”。
没多久,答案揭晓。1959年12月,他离开了熟悉又压抑的功德林,进入了一个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——。距离他上一次以要员身份步入,已经过去二十多年。身份变了,立场变了,心境自然也大不相同。
在西花厅的会见场合,出席的人不少,多为被特赦战犯中的代表人物。周恩来总理步入会场,目光在众人之间扫过,突然停住,叫了一声:“曾扩情!”声音不高,却异常清晰。那一刻,两人目光相接,这位昔日黄埔学生、周恩来早年的部属,猛然间泪流不止。
他没想到,几十年风云变幻,自己的名字还记在周恩来心中。当年的黄埔政治部主任、如今的新中国总理,在这一刻没有谈旧账,只谈今后路怎么走。谈话内容并不复杂,大意是希望他们认清历史走向,珍惜新生机会,继续接受改造,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据当时在场的回忆,有人低声感叹:“这样对我们,已经够宽大了。”如果把时间线年,那时蒋介石下令把曾扩情送进监狱时,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,他会在新中国领袖面前,得到这样一番教导与信任。
特赦后,按规定,曾扩情可以选择留在北京发展,也可以赴他处生活。就在此时,来自辽宁的儿子来信,希望他到东北安家。经过考虑,他决定离开曾经权力斗争的中心,前往辽宁本溪落脚。
在辽宁,他并没有被边缘化,而是在政协系统中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。此后,他历任辽宁省政协第四、五届委员,政协秘书处专员,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由曾经的复兴社骨干,到新中国人民政协委员,这种身份转换在个人层面上极具戏剧性,但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,又并非孤例。
1983年,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,辽宁省代表团中有一位特邀委员格外引人注意——这位头发花白、身材矮胖的老人,正是曾扩情。他以特邀委员身份,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内。相较于当年身着军装、出入的意气风发,这时的他,更多是一种沉静。
1988年,93岁的曾扩情在辽宁本溪病逝。至此,这个从四川威远走出的普通少年,走完了横跨清末、新政权建立的漫长一生。从黄埔军校的操场,到军统监狱的铁窗;从广汉古寺的木鱼,到功德林的高墙,再到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席位,他在不同制度、不同阵营之间辗转,留下的既有政治人物的复杂身影,也有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改变、不断适应的无奈选择。
回过头看,曾扩情在很多重大历史节点上的表现,并不总能用“忠诚”或“背叛”这类简单词语概括。有时他顺流而上,有时逆流而行,有时又借出家来逃避。他曾极力为蒋介石造势,也曾在西安事变中为“逼蒋抗日”发声;他曾在黄埔同学中大力清剿影响,后来又在新中国制度下接受思想改造。他的选择有功利的一面,也有情绪和观念发生变化的一面。
这大概就是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:生在旧时代,走进新世界,在大变局之中,有人一条路走到底,有人反复摇摆,有人中途折返。曾扩情属于后者。他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一号人物,却在节点处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值得玩味的瞬间,让人看到政治人物背后更复杂的人性与处境。